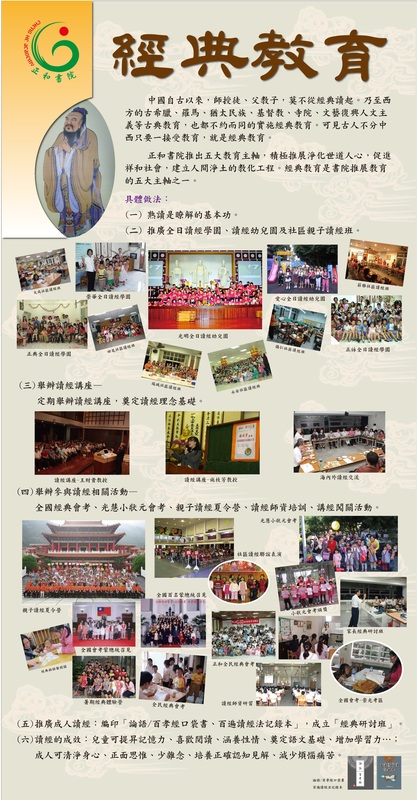|
【演說論語】
■第一部教學篇 第一集:虛心好學(一) 第一集:虛心好學(二) 第一集:虛心好學(三) 第一集:虛心好學(四) 第一集:虛心好學(五) 第一集:虛心好學(六) 演說論語:88部 (治國篇/處世篇/教學篇) |
分數離開了學校,就失去它的魅力;
不要比不重要的東西,要比長長久久跟著孩子一輩子的東西。 ~洪蘭教授 重尋古典智慧
王財貴博士訪談錄 《深圳特區報》 時間:2001年8月23日上午 地點:深圳南油酒店804房間 “讀經”,又稱“經典誦讀”。1994 年,台中師範大學語教系王財貴教授在臺灣發起青少年讀經運動,倡導教育從讀經開始,主張利用 13 歲以前人生記憶的黃金時期,讀誦中國文化乃至世界一切文化的經典,提昇文化修養,以健全的人格、道德和智慧投身於社會。“讀經”教育一經倡導,便在臺灣得到廣泛的響應。後經南懷瑾、楊振寧等諸多有識之士的倡導和推動,大陸和臺灣、香港地區乃至北美、東南亞華人社會均開展了兒童讀經活動。6 年來,臺灣已有 100 多萬兒童誦讀經典, 香港也有上萬名少年兒童在學習中受益。據統計,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漢、深圳等地至少有 120 多萬兒童先後投身其中,受其影響的成年人超過 600 萬人,武漢、南京等地甚至一度出現青少年讀經熱。 日前,兒童讀經的首倡者王財貴博士來深圳演講,本刊記者採訪了他。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在採訪之前,我們曾經收集和瞭解了一些關于祖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青少年讀經情況的報道。我們看到,由于您的首創,越來越多的華語地區的青少年兒童正受到“讀經”運動的影響,我們想知道,讀經的“經”所指的是怎樣一個範疇?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王財貴(以下簡稱王):經就是經典,是指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的著作,是經過歷史選擇出來的“最有價值的書”。 人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經典是人類歷史長河中大浪淘沙、逐步篩選出來的寶貴典籍,這種數千年篩選是需要巨大成本的,但它是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假如我們重新開始篩選,那麼即使運氣好的話,恐怕多半也要讀破萬卷之後才可能明白什麼書最好,那時候我們的頭髮可能也白了,還談什麼讀經?我們優選誦讀內容,一開始就集中精力誦讀最經典的文獻,就會使文化重演達到最經濟、最科學的效果。 記:您倡導兒童讀經,足跡遍及世界華語地區,到處作義務演講,無疑已經把它作為自己一生的重要事業。我想,這肯定已經不是一個讓少年兒童讀什麼書的問題,也肯定不僅僅是教材改革層面的問題。您應該有一個更為統一和完整的想法,對嗎? 王:是這樣。我們認為,誦讀經典是一種科學、經濟的文化遺傳方式。由于遺傳包含或者推動著創新,誦讀經典同時也就是文化創新的重要方式,兒童誦讀經典就是如此。我很高興,我們的這種看法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 依據生物重演律的假設,兒童會重演人類發展的歷史,包括人類的文化發展史。人類的文明靠語言文字交流、記錄、傳承、更新,最初祇是口頭語言,並沒有書面語言。由于沒有書,口頭語言將生產生活的經驗、知識傳承下來的方式,就是靠背誦。比如各民族的古代史詩,最初都是口頭創作、口頭傳誦的,那需要極好的記憶力。可見初民首先要鍛煉記憶力。這種能力在孩子身上得到重演,小孩子記憶力比大人好,因為剛開始學習講話的小孩子相當於處在口頭語言時代的初民,是創造、學習、鍛煉口頭語言的最好階段,他們大量重複地使用口頭語言,並在重複使用中鍛煉口頭語言能力、記憶口頭語言和其中的文化內容。當然,這祇是一個表面的問題,那就是兒童能夠成為承接文化遺傳的最好的載體。 南懷瑾先生曾經提出,要創建“中國斷層文化重整工程”,因為這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個工程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少年兒童中倡導讀經運動。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一代人身上出現了斷層,這一點在臺灣表現得特別明顯。我們倡導“讀經”教育,即是希望兒童在其性向純淨之時,及早選取傳統中有高尚意義的文化教材以教養之。 當然,教育是一個春風化雨、日積月累的過程。經典是最高的智慧,是聖賢之言,是民族文化精髓的結晶,誦讀經典可以將智慧和德性融為一體,通過口誦心思,日積月累,來完成個人文化道德修養的積累和提昇。 我在接受臺灣媒體採訪時曾經說,從人性的根源、教化的核心來說,教育的這種革新是當務之急,是“固本培元”的工作,雖然收效在十年百年之外,但“今日不做,必貽明日之悔”。 記:您最早產生這個念頭的動因是什麼?它與您曾經在台中從事國小教育有關嗎?或者說是您對臺灣教育現狀的反思促使您產生這一念頭的嗎? 王:產生這個念頭很早,那時我在台中逢甲國小任教,我做過這方面的實驗。第二次則是在 10 年前,對自己的四個小孩進行這方面的實驗,有個好朋友也把女兒送來一起學。實驗証明,孩子沒有透過現行的先理解再記憶的啟發式教學,只憑著古文的音律之美來背誦,興趣並沒有減低,而且經過一年半載,對文字的敏銳度和鑒賞力都提高了。 記: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臺灣的教育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問題,一些有責任感的學者對目前的語文教材感到不滿和擔心問題,等等。我們想知道,您身體力行地倡導兒童讀經,同這些有關係嗎? 王:在臺灣的確有許多學者對臺灣目前的教育現狀和趨勢感到擔憂。我們把目前的這種趨勢叫“去中國化”的傾向,就是漸漸遠離文化傳統的影響,割斷同文化母體的聯繫,教材也越改越簡陋,缺少文化的內涵和對心靈的陶冶,祇有知識的、技能的訓練,重視了科技方面的教育,但忽視了精神層面的教育。 我在各地的講演中多次說,“成人”之所以是成人,不僅僅是身體的長大,更重要的是心靈的長大,具有相應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和思想的內涵,否則,無異於侏儒,一種文化的侏儒。現在,我們放眼望去,這樣的侏儒實在太多了。試想想,中華民族的子孫連反映自己祖先文化成就的書一本也沒看過,甚至連打開翻翻的勇氣都沒有,不是文化的侏儒是什麼? 這種文化上的侏儒症直接帶來的就是道德的淪喪和良知的缺失。正如你所說,近年來臺灣的教育水平在提高,高學歷的人才在增加,但犯罪率卻越來越高,甚至連小學生都在犯罪。每年的暑假都會有“犯罪熱”,警察都要加班。我這次來大陸之前看到報道,一夥中學生深夜飆車,有人在路上攔截,竟然用刀砍死。問他為什麼?他說,“為了我痛快”。 倡導兒童讀經是來自對人性根源和教化核心之體察,當然自有其良苦的用心。一個孩子一出生,大體應該是一個健康的善民,後來之所以成為罪犯,是不良的教育使然。 我想,普遍恢復讀經的風氣,從兒童期就給孩子“讀經”,肯定有助於恢復國民的良知和善心,有助於社會道德水準的恢復和提昇。 記:下面這個問題可能是一部分人的擔心。因為從形式上來講,讀經很容易使人產生聯想,那就是它很像中國傳統的私塾式的教育。而現代教育對舊式教育否定的重要理由就是,它的教學方式是“填鴨式”的,它的教學內容往往是帶有封建色彩的,它所教出來的學生有可能成為“書呆子”。當然,我們未必同意這種看法,但我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的。 王:教一個民族的幼苗接受其祖先的智慧的熏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在這個時代裏推廣這樣的讀經教育,卻備受質疑與責備。你剛才所說的,就是這些質疑與責備中的幾種。在今天讓兒童讀經,與過去的私塾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環境已完全不同。 說“讀經”教育是“填鴨”,是所謂“引喻失義”。因為我們說“讀經”,是讓兒童糊里糊塗把經典“背下來”,而兒童正是處於理解力糊里糊塗而記憶力相當發達的年齡段,“背書”正是他的“正經事”,他的拿手。“填鴨”,是鴨胃小,吃不下,硬填,填了不消化,現在,兒童背誦的能力強得很,好像一頭有四個胃的牛,填多了,他會慢慢“反芻”。所謂厚積薄發就是這個道理,背了很多的經典,也許在眼前是沒用的,但有一天,這些經典的力量就會發散出來,有利於他們成就學業和專門的研究。至於說會成為書呆子,這是不可能的。過去的學生除了古文的學習就沒有別的了,所以長大會成為“書呆子”和“冬烘先生”。現在不一樣,資訊那麼發達,讀經祇是很少的時間,怎麼會成為“書呆子”? 倒是現在的語文課很成問題。就那麼幾篇文章,又沒有幾篇經典,分析來分析去,要分析一學期,歸納起來不外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寫作技巧、修辭手法等等這一套,有人戲稱為“文章八股”,但是居然要作為標準答案考。既然是標準答案,又要考,自然就需要背誦了,從小學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博士生,文科一直大量地背誦這些東西。過去,我們有篇小學的課文是這樣的:“喔喔喔,我們上學去;叮噹叮我們放學回。”就這樣一直“喔喔喔”和“叮噹叮”下去,我們上完小學,又上完大學,到研究生了,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母語還是學不好,文章寫不出來,畢業論文學位論文急得團團轉,經典文獻在哪裡找不到,因為平時盡看二流三流資料了。 記:“讀經”這個詞給人的另一個聯想是“五四”時期的著名論爭。當時有許多文化巨擘是反對讀經的。比如,魯迅和胡適之先生就反對讀經。一位當時的學者給青年人開書目單,魯迅就曾經給予嚴厲的批評和嘲笑。這雖然是上個世紀初的事,但我想,您不可能不對此作反思和關注,因此我們仍然想知道您對此的看法。 王:五四時期許多文人之所以持“反傳統”的心態,是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有關的。雖有合理的一面,但今天看來仍然偏激。本來,“反傳統”,如果是“反省傳統”,則是表示一個民族的要求進步,這是任何一個有活力的民族常要做的事。但“反傳統”如果變成是無條件的“反對傳統”,乃至於必須“消滅傳統”才甘心,那就不同了。“消滅傳統”只能使一切傳統的傳承汲取皆失其根源。如果說昨天是從“根”拔起,那麼今天我們推廣誦讀經典即是要從“根”救起。 記:我們注意到臺灣媒體對您的稱謂,“新儒家”學者。著名的文化學者湯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在談到世界文明古國衰落的原因時有一個觀點,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重蹈古埃及和古羅馬的覆轍,一個重要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想問的是,您倡導讀經運動,主張復興儒家文化,同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維護民族團結一統這樣一種願望有關嗎? 王:我完全同意湯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的觀點。文化的復興,民族的團結一統是題中應有之義。
兒時讀經終生受益
載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8月9日 最近臺灣王財貴博士在新加坡推廣“兒童讀經”法,這是件大好事。雖有個別人持異議:認為水土不服,小孩子不會感興趣,這是“填鴨式”教學,不如多背其他有用的東西,包括英語單詞等,但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 我是大陸極少數從兒時讀經出身的中年知識分子。我今年45歲,按理說,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麼會走上讀經的道路呢?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還以為大陸有讀經土壤。事實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儒經已被批倒批臭,很多研究者都不讀了,他們祇是撿幾句話來寫“大批判”。 我出身農家,遠祖有什麼輝煌已不得而知,從我曾祖開始,就是老老實實的農民。不過,我母親的娘家卻是書香門第,外公和舅舅都讀過“大書”。我兒時在母親的教誨下,能背誦《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的個別章節等,但由于母親並沒有上過學,外公家只準男孩讀書,母親是自己偷習的字,所以對這些經文她有的能說清含義,有的說不清。我那時讀經是名副其實的囫圇吞棗。 1966年,大陸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小學也停了課。我在家沒事,表哥給我找了《詩經》、《尚書》、《左傳》、《四書》等來讀,雖然讀不懂(表哥是醫生,對經書只知皮毛,不能做我的老師),但覺得挺好玩,就自覺地一段一段地背,而且越背越多,越背越快,有時一篇幾百字的文章,讀三四遍就能背下來了,短的讀兩遍就能背了,當時也不知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勁。我背書完全出於興趣,沒有壓力。 我讀經的第一個收穫是險遭迫害。因為當時正值文革,“破四舊”、“立四新”,我讀經就成了封建殘滓餘孽。我在學校雖然當了班幹部,但從校長、老師到同學都認為我思想舊,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書(抄家)。幸虧我出身貧下中農,祖宗八代都沒乾過壞事,自已又頭上沒辮子,屁股上沒尾巴,才做罷。不過這對我的前途還是有影響的。 我讀經的真正收穫,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我由東北農村,一舉考上廣州中山大學。文革後首屆高考,雖然考題不難,但考中卻極不易。因為從文革初的1966年,到文革後的1977年,社會上已積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祇有千分之幾。 我考上中山大學,在當地不遜於範進中舉。不過,從兒時讀經是我金榜題名的關鍵,因為經學對理解語文、歷史、政治、地理均有幫助。至今還記得,我們吉林省語文考題的古文翻譯是《左傳•曹劌論戰》,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來,所以當時我只看了一眼,便刷刷刷地將其全部譯了出來。 我的經學研究在大陸可謂“迷宗拳”,沒門沒派,全都是自悟。這有一個好處,就是思想無拘無束,能做到真正的解放。無論在研究方法上,還是資料的占有上,以及學術觀點上,我都有創新,先後發表了一批在中國古史、經學和子學研究上都有一定影響的論文,如:《中國古史分期新探》、《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董仲舒非儒家論》、《韓非非法家論》等。 這些論文,其中大陸最有影響的綜合性文摘刊物《新華文摘》轉載一篇,摘要多篇;《報刊文摘》轉摘兩篇;人民大學複印資料《歷史學》等轉載三篇。此外,有的論文還被收入大陸的一些學術叢書,我的名字也被編入較權威的“學人辭典”。 回顧我從兒時讀經到現在,體會有五: 一、兒童讀經很有必要。作為龍的傳人,應瞭解自已民族的文化史,應從小打個好基礎。既便是西方對中國傳統文化感興的白人,讓孩子從小讀點中國的經書,亦大有益處。 二、兒童讀經方法要講究。先要想辦法引起兒童讀經的興趣,然後在背誦上作文章,儘量少講解,讓其自悟,悟出來的道理才深邃。讀時不要由淺入深,而應由深入淺,從《詩》、《書》、《語》、《孟》、《易》、《禮》、《左氏》等入手。由深入淺學習,如從山上滾石頭,越學越容易,興趣也越高,若從淺到深,則步步維艱。因為此時兒童對經文不要求甚解,深和淺對他都一樣,背熟了將來就會懂。 三、兒童背經不是“填鴨”式教學。兒童背經,祇是利用其年少記憶好的特點,讓其機械記憶,不是將經文的所有涵義都讓他弄懂。背能鍛煉記憶力,背的目的是留待他將來自已去“悟”。悟是思想自由,能啟迪其理性思維,不存在“填鴨”的問題。相反,大陸教師講課滿堂灌,強令學生死記硬背,再加上“八股”式的考試,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填鴨”式呢。 四、背經要比背其他的東西更有益。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線與精髓,兒童背經不僅能瞭解古代思想文化,也對歷史、文學等知識有所把握,而且觸類旁通,還能懂得做人的道理。其他東西固然也要背,如外語單詞,但學習外語單詞不一定在兒童時期,年紀大點也能學好,經學則非要在兒童時背才能記得牢,否則就難以刻在心中,日後也很難悟出真諦。 五、兒童讀經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問題。孔子的仁當時雖是為中華民族而設計的,但實則是全人類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祇要有人的地方皆可,有華人就更好。 傳說當年楚王遺失一弓,被楚人拾去,他就不找了,說:“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孔子聽了,批評道:“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可見孔子崇高的人類主義精神。孔子的仁祇要有人的地方就能被理解和發揚光大。現在西方的儒經研究已蓬勃展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正像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棗黃河已幾經斷流一樣,經學在大陸早已衰落,大陸學子正如湯建國教授所言:都在多背外語單詞,忙去美國深造,忙拿美國綠卡,視儒經為駢拇。經學當此危難之秋,王博士奔走於新加坡,推廣“兒童讀經”法,華夏幸甚,天下幸甚!孔子說過:“周公既沒,文不在茲乎!”信矣哉!信矣哉! |